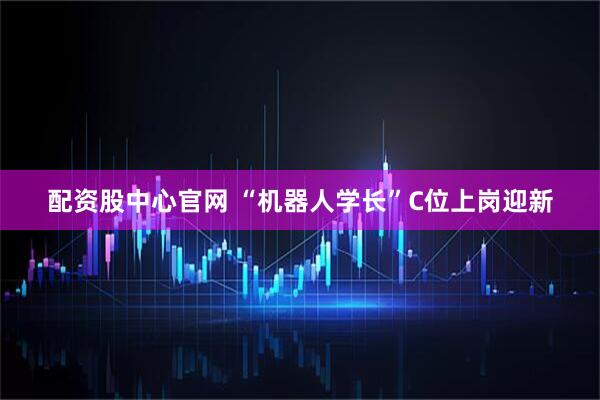社交媒体上配资股中心官网,「原生家庭创伤」的讨论铺天盖地,仿佛成了年轻人「标配」。
父母辈经历过物质匮乏的艰苦岁月,却很少听说他们大规模地抑郁。
是因为现在的小孩更脆弱吗?抑郁的诊断被泛化了吗?是人均矫情,拿抑郁症来做逃避责任的借口吗?
答案远比想象复杂。

在父母辈成长的时代,精神卫生知识极度匮乏,社会整体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几乎为零。
DSM-5(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)和ICD-11(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)都明确指出:文化背景和时代观念深刻影响着心理痛苦的表达、识别与归因。
当时许多符合现代抑郁症、焦虑症诊断标准的痛苦体验,常常被归咎于以下几点:

在缺乏安全情感表达渠道和社会污名化的压力下,心理痛苦往往通过身体「说出来」。
失眠、莫名的疼痛(头痛、背痛、胃痛)、长期乏力、食欲不振、心慌气短等成为更「安全」、更易被接受的表达方式。

《Why We Sleep》(Walker, 2017)中详细阐述了慢性压力严重破坏睡眠结构。
长期失眠既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,也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。
许多父辈的「睡不好」、「浑身没劲」、「老毛病又犯了」,其背后可能就是未被识别的抑郁或焦虑。

我国早期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受限于方法学、诊断标准和公众意识,抑郁症的检出率极低。
例如,1982年全国12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,情感性精神障碍(包含抑郁症)的时点患病率仅为0.76‰。
这远不能反映真实的痛苦水平,更多反映了识别和诊断能力的的历史局限。(张明园等,1985)

童年不良经历(ACEs)的科学性毋庸置疑。
大量研究证实,童年期经历的虐待、忽视、家庭暴力、父母物质滥用或精神疾病、家庭功能严重失调等创伤经历,是成年后罹患抑郁症、焦虑症、物质依赖及多种躯体疾病的显著高危因素。

“原生家庭创伤”讨论兴起的本质上反映了科学知识的普及(对ACEs危害的认识)和心理健康意识的觉醒。
虽然表达有时可能过于泛化或简化,但其指向的童年逆境对心理健康的深远负面影响,拥有坚实的神经生物学理论支持。
最新研究表明:
严重的童年创伤可能通过表观遗传修饰(如DNA甲基化、组蛋白修饰)影响基因表达。
这些改变不仅影响个体终身,甚至存在跨代传递的可能性。
这意味着父母未化解的创伤,其生物学印记可能潜在地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基础(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, 2023)。

父母辈也并非没有经历创伤或未受影响,而是这些影响未被当时的人们科学认知,也并未被社会话语所识别、命名和公开讨论。
许多父母自身的创伤经历(如他们童年经历的贫困、动荡、甚至更严厉的教养方式)可能未经处理,一直以来无意识地影响着他们的养育行为。

我们要清楚一个概念:诊断率飙升≠患病率暴涨。
近年来,中国报告的抑郁症患病率数据显著上升。
《中国精神卫生调查(CMHS)》显示,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6.8%(Huang et al., Lancet Psychiatry, 2019)。
这主要反映了诊断识别能力的大幅提升(更规范的诊断标准的应用)、精神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改善(尤其在大中城市)以及公众病耻感的缓慢降低。
就像海平面下降,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变大了,并不是冰山本身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大了。

我们也有理由推断:
父母辈中经历的符合现代抑郁症诊断标准的痛苦,其真实比例远高于当年极低的流行病学数据。
他们的抑郁,是沉默的「水下冰山」。
父母辈在物质匮乏年代展现坚韧,但这绝不等于他们没有经历过内心的痛苦。
他们的痛苦被时代贴上不同的标签,或通过躯体承受,用失眠和疼痛表达,或在「坚强」叙事中被掩盖。

年轻人对「原生家庭创伤」的关注也并非矫情。
这是心理健康意识提升、科学认知进步以及对自身精神福祉正当追求的体现。

代际差异的本质,是社会历史背景的巨变、精神医学认知的飞跃、环境压力源的转型以及个体表达权利获得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与其评判「哪一代更苦」或「哪一代更脆弱」,不如怀着同理心,去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应对苦难的不同方式。

重要的是:
无论生于哪个年代,心灵的痛苦都真实存在,都值得被倾听、被理解、并得到科学的关怀与疗愈。
如果您恰好需要帮助,安忻一直都在。


审核医生:彭旭
插图:金三儿
免责声明
本科普文章之目的是提供普适的健康信息,内容均为科普知识介绍,不含有推荐、证明等广告属性。科普内容不能代替任何人的医学诊断和治疗方案,如有需求请您及时就医。作为科普文章,本文中如出现极限词,为医生临床经验中的个人认识或学界共识,是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其客观重要性的表述,无广告属性。如对这篇科普文章有任何建议,或对文中来自网络未能找到出处的图片有版权异议,请发邮件至安忻品牌部:tangsj@axnsleep.com。
捷希缘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